
上世纪40年代,父亲曹禺和母亲邓译生在重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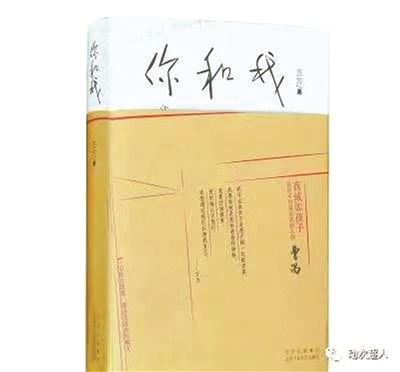

童年万方和母亲

万方和乖乖
“人们习惯为尊者、亲者讳,万方女士却全然诚实地交付了。于是我们看到人的软弱与无奈、激情与温情、世人的悲苦、自己的折辱、本质的孤独与孤独中依然向爱敞开的心……他们的故事固然与时代相关,但其实这一切又是任何时代人的母题,唯有坦然接纳。”
万方老师父亲的故事,不是第一次听。学过中文的人,谁不知道曹禺呢?神一般的天赋,悲歌般的凋零。关于她的母亲,记忆中却只有一句,万方老师亲口告诉我的:“我妈妈死的时候,身子底下就满是药片。”印象中骇人的一景。
那是2014年,我去和她聊话剧《冬之旅》。6年过去,万方老师音容未改,而我不一样了,我也失去了母亲,我的父亲也让我看见更多苍老。坐下来,我觉得,我更能听懂她的话了。
初见《你和我》,是2019年8月,《收获》双月刊第四期。第一次通读,是今年4月底,距它完稿整整一周年。再读,是6月初,那时已约好万方老师,我们聊一聊它。
如此郑重,只为配得上它。
关于《你和我》的读后感想,目力所及,没有人能比主持人张越说得更好:
母亲她幸福过吗
北青报:这本《你和我》写作历时一年半,听说动笔前用了十年时间来纠结?
万方:可能十年都说少了。我想写,一定要写,但是写不了,还得克服心理障碍。就一直在这样的过程中。
北青报:“一定要写”的是什么?
万方:写他们的爱情。因为我手里有他们的情书。我都不知道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被抄家、被占房子如此种种以及几十年的时间,我爸妈是怎么把它们保留下来的。
我用了很长时间(因为我爸的字只有我认识),一点点把它们都整理出来。然后我才想到我妈这一生,其实她也很幸福过的。因为像我爸那种爱情——那种强度,那么炙烈,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够享受到的。这个可能是最初我想写的。
但这是不是一切?肯定不是。因为还有我记忆中我妈痛苦的那一部分。在我的印象里,从我懂事之后,想起她来我就难过。确实就像我在书里说的,她带给我的都是痛苦的记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写了这本书,慢慢捋她的一生,才慢慢回过味来,替她想她还是幸福过的。可能,我觉得我没为她做过任何事情,这个也是我难过的一部分吧。
所以我想的就是要真实,写她,写我爸爸,一个女儿心目中所能够记忆起来的最真实的爸爸和妈妈。我觉得这个大概才是全部。
北青报:那“心理障碍”是障碍在哪儿?
万方:就是我书里也提到的,在她跟我爸不能结婚的那十年,我妈虽然那时候是一个年轻姑娘,但她也是一个“第三者”。这一层不知道怎么让我就这么难以跨越,觉得这是拦着我的一个心理障碍。
北青报:拦着你去理解,还是拦着你去讲述?
万方:拦着我去讲述。理解没有问题,我也写过很多不同的作品,从小说、戏剧到影视。我自己在书里也说了,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你想我自己的经历,其实我也是离过婚的。我为什么呢?我弄不清。所以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人性。你创作是一回事儿,或者你自己切身的选择是一回事儿,但是在你心中最深处,涉及到最疼爱你又离你远去的最美好的母亲的时候,那个东西一下就变得很强大很有力了。
北青报:我之前还以为最难的是关于她服用安眠药过量的部分。
万方:服药属于她生命痛苦那一部分,那是肯定的。关于服药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如果要写,那我绝对要真实表达。否则的话,我觉得我对不起她。如果我只表现想象和记忆中好像是很温情的东西,那没意义,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本书从不能写到慢慢我觉得能写了,实际上对我自己是一种心理治疗。过程不是不痛苦,但写完之后,我真的觉得自己比原来强大了。包括我对周围事情和人的那种感受都不是没有变化,我比原来更能够做我自己了。原来可能我被种种困扰束缚着,现在通过写这本书,我把这种束缚挣脱了。
北青报:什么样的挣脱呢?
万方:包括所谓道德观念,包括种种顾忌,包括对周遭世界我不该在意的在意。比如你回避她吃药的那种惨状,因为你怕人知道,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妈妈那么悲惨。我觉得这些都是束缚,那么我克服这些。现在我所谓的强大,就是我明白有些东西不要在意,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这是这本书写了之后我自己的一种感受。
梦里总是找不到妈妈
北青报:整本书从妈妈的死开篇,“发现她死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掀开盖在她身上的被子,她的身旁身下全是药片,安眠药。她不是自杀,是吃多了药,吃了又吃,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她的问题是离不了安眠药,依赖它,1974年7月的这个夏夜,安眠药要了我妈妈的命。”您后来把这个场景写进了您的话剧《冬之旅》。
万方:其实我书里倒是直言不讳地说了,其实药吃到那个程度,其实就跟吸毒差不多。安眠药可以让你忘却一切、忘却痛苦。忘却痛苦对他们来说,也就算是一种快乐了吧。
我爸一直吃,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爸得了神经官能症之后,就吃安眠药。但是我妈很长一段时间再不吃了,然后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吃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为什么先写这个?因为我必须先写,把这个门撞开。从最早我就想好了,如果写,我第一件事就写我妈走。因为这个对我是最痛苦的事,我必须先把它给趟过去,我才能往下进行。
北青报:可能这个给您的震惊也太大了,是不是?
万方:所有我所谓说痛苦,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北青报:您从沈阳赶回家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没有那个现场了。
万方:没有。邻居,一个阿姨,她跟我们讲。妈走的时候我是不在的。我回家她已经尸体都运到医院太平间了。
北青报:您到医院见的她?
万方:对,我不是还说我给她找衣服。但是我爸没去,他就是没去,他就躺在小书房里。
北青报:躺了很久是吧?
万方:躺了很久。后来到我们都回部队了,他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小书房里躺着,整个人都不行的。
北青报:那回去这一个月,除了去公园划船,您在家里也得照顾他吧?
万方:我不记得。说老实话,我不记得我照顾他。
北青报:您有没有觉得很害怕?
万方:没有,我不记得。那时候家里还有一个阿姨呢,要不说我爸人缘好,我爸在人艺那时候不是都减工资吗?人家给他算工资还算出一份阿姨的工资钱,所以他一直还能够有一个阿姨。所以可能做饭都不是我们做,有这个阿姨做。
那时候,要不我在书里写“青春是残酷无情的”,真的,你都想不到你要去跟他交流,去安慰他,或者去向他表达什么。我都不记得,没有,应该说是没有。
后来我就想到自己,其实在十几岁二十几岁年轻的时候,你难过是难过,但是很快就有其他的事情就把你给吸引了。我觉得那是一种“青春的能力”吧。其实真正难过是我成熟了、大了,我才会对我妈妈感觉到越来越难过。
我总做梦梦见我妈,所有的梦都是找她,哭醒了,找她,哭醒了,找她。永远,到今天为止,梦里我都没找着过她。我想,就是因为我觉得她走的时候我不在。再有,我没为她做过任何事。
北青报:有没有为妈妈的事怪过爸爸,也没有?
万方:没有,一点也没有。真的谁我都不怨,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是吧?如果是我,我会不会呢?我可能也会的。这也许就是刚才你说,最喜欢我书里的那句——“爱,就是爱人性的弱点”。
曾经我不懂父亲的病
北青报:《你和我》初衷是写妈妈,但是也有大量的篇幅是写爸爸。
万方:其中一个原因,确实我对我妈妈了解不多。1974年她走的时候我22岁。我16岁就离开她去农村插队,18岁去部队当兵。之前我还是中学生。我还没有机会也没有准备好去深入地了解她。
那天跟演员剧雪聊起对父母的了解,我说其实孩子很少关注自己的父母,孩子更关注自己的同辈人,身边的朋友这些。人在小的时候,父母虽然跟自己最亲,天天在一起,但是你并不理解他们,也不了解他们。
我妹妹总跟我说,你要写写妈妈幸福的时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从来不觉得她幸福。可能因为那时候很小,你觉得所有你身边的事情,包括爸爸妈妈他们的关系,他们怎么过,都是日常,就是像流水一样的日子,时光就是这样的,你不会特别地去体会到她是不是幸福。
写这本书最主要是为我妈妈。但是不可避免,你说我曹禺的女儿能够不写曹禺吗?自然而然。
北青报:而且对于您母亲来说,她没有出去工作的经历,日常就是书画为伴,对于她来说家就是她的世界。她的幸福与否,就是直接与家人相关。
万方:是的。她一直就是一个很自我的人,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她不是那种和外界去交往的人,她自我的这个世界是很难被攻破的。
北青报:那您父亲快乐吗?
万方:他是真心地对新中国,对这一切都充满了热情。但他五几年就得了神经官能症。
北青报:对那个您有印象吗?他表现是什么,睡不着觉?
万方:睡不着觉是很久很久以来就是了。他那时候住院,我不懂,我大概听他们大人说,说他站在高处就想往下跳。我一点不理解,那时候我是才几岁的小孩,我去医院看他,心里还想:我爸哪有病啊,这不挺好的一个人吗?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步,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他1956年入党了。他后来要求进步,要去写工农兵,但是他写不了。那时候,让他去写售货员、先进工作者,他去打酱油、卖西瓜,做这些事情去体验生活,还写抗洪。
六十年代初北京有一次发洪水,他去抗洪,跟那些老乡还成了朋友。我记得我们住在张自忠路的时候,那些老乡,都是河北的也不远,有时候到北京来还到家里来玩、来做客。但是他写不出来。我想他心里是有标准的,达不到那个他认为好的标准,他就没法放过自己。
老舍先生不是还写过一些能够赞美新社会的戏吗?我爸也写出了一部《明朗的天》,写知识分子改造的,写大夫。为此他在协和医院生活了很长时间,一两年吧。他就写了这么一部戏。后来写《胆剑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全国要卧薪尝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全国各个剧团都写,不同剧种都有。他那个《胆剑篇》,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剧吧,还是挺美的,我的印象。
戏剧天才的晚年
北青报:您没有回避父亲再写不出东西来这件事。
万方:对于他写不出东西的际遇,尤其晚年,我还是都写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写也没意义,不是一个真实的他。人家会不明白23岁就写出《雷雨》的这么一个人,《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一部一部,正当盛年,怎么就再没有了?
北青报:如果没有后来他要改造自己,他要是顺着他原来的路子走……
万方:我觉得他应该很了不得。你想想他1942年写出《北京人》,他1910年生人,30出头能写出这么棒的东西来,那很难估量。我觉得,会很棒,我是这么想。其实他真的是一个戏剧天才。不过也很庆幸了,还是留下了这4部。
北青报:您父亲到处去忙开会、颁奖什么的,那也是持续很久的状态吧?
万方:对自己那种生活状态,其实他内心里,还是很纠结的。你想想一天到晚到处去开会,不是颁奖、接见外宾就是作为专家看戏……
北青报:他一方面觉得在耽误时间……
万方:但是如果他一天没那些事,他又觉得很空虚。所以有事情他也积极地去,但是晚上回来又会很懊恼,没有一天他不懊恼。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在最亲近的人里,他会肆无忌惮地表达。有时候想他真是很可怜,他那么真诚的一个人,到最后真在外面,还有人说他虚伪呢。因为他看任何戏都是“好”。所有的戏到北京都请他看,他没有说人家不好的。因为他确实理解写作太难了,不光是你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尤其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自己都写不出来了,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黄宗江,算他的学生辈了,后来写个剧本给他拿来,上面写着“万先生,送上‘真不易’一份”。因为他看谁最后都是“真不易”。
北青报:您在书里引了他1986年写的一首诗:
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
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
万方:这是他很极致的一种情绪表达。他是一个感情强烈的人,所以他写不出来他真的不甘心,觉得这口气憋在那里。
北青报:那太痛苦了,看着都替他很痛苦。
万方:对,他是挺痛苦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也挺幸运,能够在他身边,看着这么丰富的一个人,也有助于我对人性的理解吧。没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我真是这么认为。
北青报:就像您说的“爱父亲,就是爱人性的弱点”。
万方:因为他身上真的有很多很多人性的弱点,但是你不爱他吗?你爱他。而且说老实话,一个没有弱点的人,有吗?那是不真实的。
唉,这本书写得我真是很是投入。中间真的有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我血压都高了,我去医院看病,一量血压170多,大夫立刻说“开了药你马上就吃”。可我原来是个低血压的人。等我这本书写完,我的血压就又恢复正常了。
过程中,一直都在一种心里老是揪着的状态。即便写他们爱情,包括看他们的情书,心里都有一种特别强烈、说不出来是什么样的感情,是觉得愉悦?还是觉得痛苦?还是为他们……说不出来。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爸爸自己知道他软弱
北青报:父亲身上什么地方您会觉得是他的弱点?
万方:他很软弱,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你想想我妈去世他都不敢去了,他不愿意、不想、也不敢面对。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吧?就更何况他在政治运动中。我爸自己知道他软弱,他怕,胆小怕事。
再有包括所谓的各种活动他要去参加。对于有些虚名,你说他没看透吗?看透了,那你为什么还欣欣然地去接受,是吧?书里我写到有一次活动我得陪他去,我故意离得远远的,他上台了我就不上台,他都生气了,说“你什么意思嘛!”他觉出我对他这样的表现不满。
北青报:什么样的活动?
万方:各种。任何演出他都要去上台接见演员,跟人家合影什么。但是人家说话他又听不见,需要我在旁边。我就没上去,他就老远叫我。其实他知道我不喜欢他这样。
包括吃安眠药这件事。我书里也写了,他为写《王昭君》到新疆去,大家围着他坐,等着他说话。你说那安眠药不吃了,行不行?他就要吃。然后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因为人已经就昏昏欲睡了。你说我尴不尴尬在旁边。
北青报:那他这个药,药劲够大的。
万方:他吃得多呀。“文革”时候他曾经吃得三天三夜人就没醒过来,那时候我不在他身边,他起来上厕所,就这种玻璃,摔倒撞碎,满脸是血,他都不知道,早上起来脸上血全都干了。
这都是他软弱,一个坚强的人就不会。他就是一个痛苦,他要回避。没别的办法的时候就是吃药,我不看,我昏过去,我闭眼。
北青报:像这些有没有让你害怕过?
万方:那时候年轻。我不是曾经给他写了一封信吗?他后来特别受触动,把药全扔了。结果人就不行了,整个嘴唇肿得呀就吓人。
北青报:戒断反应是吧?
万方:对。他不吃不行。我后来在哪儿看到一个说法,说人60岁之前可以戒安眠药,60岁之后千万要谨慎,不要随便戒安眠药,如果你一直在吃的话。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