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巴尔加斯·略萨收到一封信,写信人抱怨了一通西班牙有多糟糕,但最让他痛苦的还是修改书稿的工作。“我删掉了很多东西……几乎完全重写了最后一个部分……现在咱们等着瞧这本要了我老命的书会有怎样的命运吧。”
写信的人名叫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古巴作家,曾获得1997年“塞万提斯文学奖”。他信中提到“要了老命”的书,就是拉美“文学爆炸”风潮中最独特、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之一——《三只忧伤的老虎》(Tres tristes tigres)。因凡特出生于1929年,父母是古巴共产党员,他自己也曾经是卡斯特罗的支持者,上世纪60年代,他离开古巴开始流亡,先短暂居住在西班牙,之后定居伦敦直至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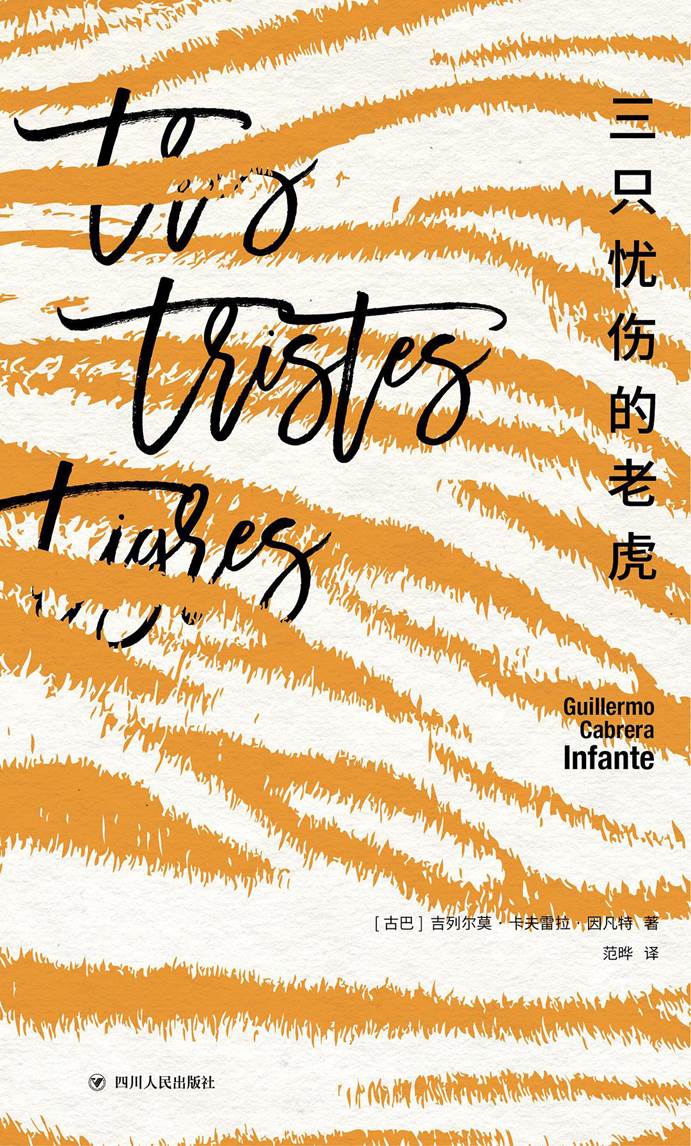
《三只忧伤的老虎》中译本
Tres tristes tigres在西班牙语中是一句家喻户晓的绕口令,类似中文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样的书名给翻译该书的各国译者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虽然直译为“三只忧伤的老虎”,但小说中一只老虎都没有,也缺乏连贯的情节和清晰的走向。小说主要人物有城市浪游者、演员、作家、鼓手、摄影师,写的是都市的边缘人以及他们在哈瓦那的夜生活。有评论认为,小说真正的主角并不是艺术家,而是文学、电影、音乐以及作者回忆中的哈瓦那。因凡特意识到,自己终将失去哈瓦那,只能在追忆中用一词一句当作一砖一石来重建这个城市,评论家称,他是用语言再造了一个故乡。

《三只忧伤的老虎》新书分享会现场
2021年7月,由行思文化策划引进、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只忧伤的老虎》中文简体版与读者见面。7月25日,《三只忧伤的老虎》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单向空间东风店举行。北京大学西语教授、《三只忧伤的老虎》译者范晔,作家苗炜,北京语言大学教师、译者李晖与到场读者一起畅谈这本“奇书”和拉美“文学爆炸”。分享会由行思文化总编辑杨全强主持。
主动读者和被动读者
说到充满语言狂欢的小说,苗炜的印象是“特别痛苦”。《三只忧伤的老虎》也是如此,对于不熟悉作者、不熟悉古巴的读者来说,会造成很大的阅读障碍。对此,范晔表示,不只是中文读者,即使是西文读者也会有困惑。“这本书看起来还挺好玩的,但看下去会发现它比较碎片化,好像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段的感觉,整体上确实有点把握不了,需要花点工夫。”
由此,范晔提到了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关于“主动读者”和“被动读者”的观点。所谓“被动读者”,喜欢读相对传统的——如线性叙事的、故事情节明显、人物刻画比较吸引人、一般意义上可读性比较高的作品,读者只要跟着故事线走就行。而主动读者则面对不同的情况:作家不给出现实情节,或是类似于洗牌,将现实情节打乱后交给读者。在这种情况下,读者是“同谋”,不是干看就行,而是要参与其中。范晔说,从某些角度来说,这类似于艾柯所谓“开放的作品”的概念。小说写好后出版,某种程度上还有一种未完成性,需要每位读者用自己的情感、智力和细致阅读,拼出清晰的线条,来完成它。“这本书不是那么典型,但也有一点这方面的特点。它确实不以情节取胜,也无意于此。但你不能说它完全是碎片,作品中前后情节还是有相互勾连,草蛇灰线的,只是可能需要你看到最后。”
在李晖看来,《三只忧伤的老虎》很有质感,“不要看,要去听,把它还原成声音”。他特别提到小说开篇一个夜场主持人在俱乐部的大段发言。小说中有两处对于主持人的介绍,一处说他是幼稚、天真但很真诚的家伙;另一处说他是不懂装懂、自作聪明的蠢货。李晖认为,这个主持人是环境的一部分,而俱乐部实际上是古巴社会的缩影,很多重要人物都在其中出现。同时作者制造了一种声音,在气氛上定了基调,整个小说是跟着声音走的,而声音是有时间线的。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在讲故事,故事的意义就在讲述本身,讲述者在这中间去进行一种记忆的练习。对此,范晔也表示,“这本书是对一座城市、一个时代或者一伙人的追忆”。小说结尾的一段独白中,作者不间断地插入了几十个“在沉默中”,这是因凡特有意为之。写作小说时,因凡特已经离开了哈瓦那,远离了自己的精神故乡。“他写作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想讲述对他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的、美好的、重要的时代——1959年以前的古巴,准确说是1959年前的哈瓦那,再具体点说,是1959年之前的哈瓦那夜生活。他觉得这个时代已经不会再有了,眼睁睁看着它消失。”
译者即叛徒?
小说结尾部分,人物之一西尔维斯特雷和人在酒吧聊天时,发现兜里装着杂志主编GCI(因凡特名字的缩写)给他的一张便条,请他重新将一位美国作家的短篇小说译成西班牙语。这篇小说之前由一位叫做里内的人翻译过,但因为翻译很糟糕无法刊发,故而主编请他重译一稿……最后西尔维斯特雷回到家,陷入半梦半醒之间,想到一个意大利语词汇“Tradittori”。
“Tradittori”意为叛徒,据传出自但丁的名言“译者即叛徒”——译者在翻译时,实际上是出卖、背叛了原文的意思。范晔表示,作者在故事中有意提到很多处错译,用“译者即叛徒”结尾,表明很多翻译都是靠不住的。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模式,由此引申出来一点,写作或文学本身甚至语言本身也是不可靠的,“但这里有一个悖论,他自己说语言不可靠,但这个观点本身也需要用语言来表达,而他并没有说因为语言不可靠就不说了”,在某些方面,小说也表达了作者对文学本身和对语言本身的一些看法。
范晔介绍说,小说的几个主要角色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很奇怪——牾斯忒罗斐冬。“牾斯忒罗斐冬”是古希腊一种修辞手法,意为“牛耕式转行写作法”,指行文像耕牛犁地一样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如此反复。“牾斯”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牛,因此在翻译时,范晔有意用了带有牛字旁的“牾”字,在现代汉语中,“牾”字最常用的造词法是“牾逆”,有背离和背叛、抵牾的意思。他认为,这个人与其说是小说的一个人物,不如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导师。小说中,在“不同古巴笔下的托洛茨基之死,事发后——或事发前”一章中,作者戏仿了七位古巴重要作家(何塞·马蒂、莱萨马·利马、比尔希略·皮涅拉、莉迪亚·卡夫雷拉、李诺·诺瓦斯、阿莱霍·卡彭铁尔、尼古拉斯·纪廉),用戏谑的笔法讲述了托洛茨基遇害这一重大事件。这些戏仿写作有很多阐释的空间,其中一层含义为它们其实是牾斯忒罗斐冬的作品,不是他写下来的,而是几个精神弟子记录的他戏谑的讲述。牾斯忒罗斐冬坚持认为真正的文学不应该写下来,而是说出来的——真正的文学应该写在空气里。“他用戏谑的笔法把这个故事写了七遍之后,你会觉得有什么地方开始产生变化,有时候可能会重新思考什么是历史,或者我们熟悉的那些重大叙事是不是可靠。”
“骑虎难下”的翻译之路
在《三只忧伤的老虎》的试读本中,编辑提醒读者“这本小说的语言使用极为任性,版面安排也很无理取闹”,书中有很多作者有意为之的错别字、文字游戏,突如其来的黑页、空白页,甚至还有一页的文字是反着印刷的。这样一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阅读具有一定困难的小说,翻译成中文的艰辛,只有译者范晔知道。
“当时我的一个老师,西语界的前辈,就劝我说,你别接这个……这个事不好弄”,范晔说要不要接下翻译他犹豫了很长时间,仅仅在书名的翻译上就挣扎了很久。直译为“三只忧伤的老虎”,意思准确,却没有了西语原文中语言的游戏感和绕口令一样的语感,为此他还曾想过“虎苦图”的译法。为了翻译这部小说,范晔特意拉了个电影单子,去看了很多老电影和照片:讲述哈瓦那音乐“老炮”的《乐满哈瓦那》、因凡特本人担任编剧的《迷失城市》以及老照片中哈瓦那的著名景点、也是小说重要舞台的滨海大道……他自称这样可以“原地夜游哈瓦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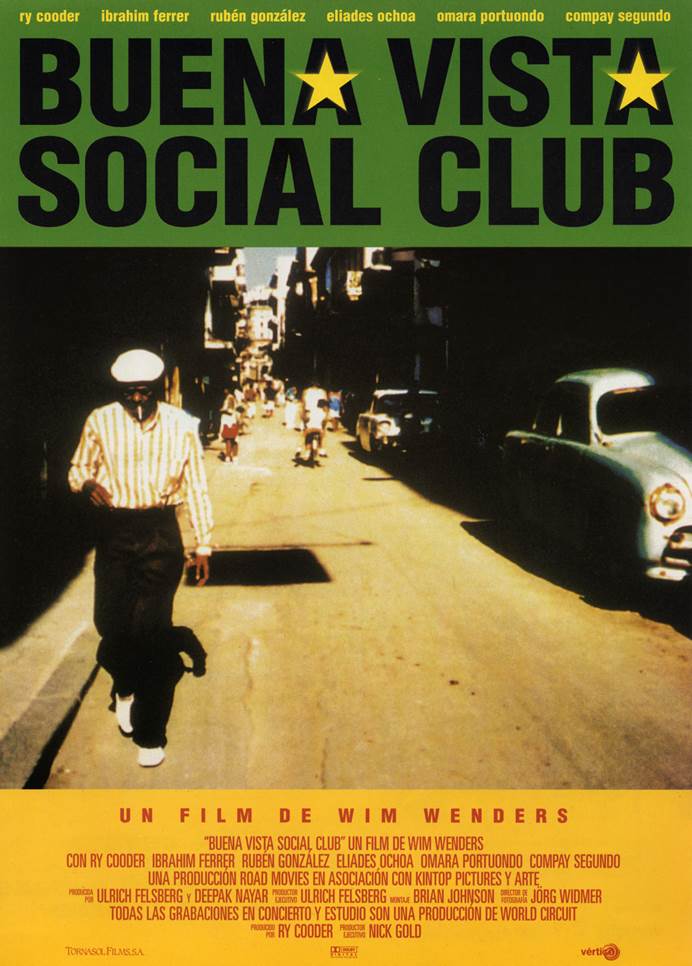
《乐满哈瓦那》电影海报
范晔想了一些办法来帮助翻译。他收集了小说各语种的译本,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的译本,请教了各个语种的专家,包括与做古巴文学的同行共同讨论,来帮忙理解作品中的表达和翻译策略。英法德等语种的译本处理比较类似,因为同为拼音文字,对一些典故或文字游戏可以不用翻译,或者稍微做一下替换即可,但中文不能这样处理。反而是日语译本面临着和中文表达一样的困难,比如日语译本中,译者用东京腔来替代了小说中一些非常哈瓦那的表达,翻译得比较灵活,日语读者能够从译本中读出很明显的地域特征,“这给了我一些胆气”。
《三只忧伤的老虎》中译本有大概1000个左右的注释,范晔说,“这个东西要都很忠实地‘贴着翻’恐怕也会比较糟糕,游戏性就因此损失太多。如果看我现在译本的呈现,实际是妥协的结果,有些我是‘贴着翻’之后加注,但这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原来的注比现在还多,我还删了一些”。
还有前文提到的对于七个古巴作家的戏仿,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有挑战:“你要想看明白戏仿,前提是你得知道它原本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七个古巴作家里面,其实真正有译介的就是两个,一个是何塞·马蒂,另外就是卡彭铁尔。”大家不熟悉或没有读过的作家,这样的戏仿不太容易看得出来。范晔的想法是,尽量让这些文本有区分度,如果七个人的文本在翻译后看起来差不多,那就彻底失败了。考虑到单凭一己之力译出七个完全不同风格的难度,范晔更多用力在对何塞·马蒂、莱萨马·利马、卡彭铁尔三位作家的戏仿作品,希望这三个作家能各有面貌,“说不定我们中文读者会借此去找原本来看,也挺好的。如果有这么一个意外的收获,我觉得我的工作从这个角度上也还有点价值”。
“文学爆炸”的边缘人
有评论称,《三只忧伤的老虎》是“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英语文学包括乔伊斯对于因凡特的影响很大。离开古巴后,因凡特常年生活在伦敦,后来加入英国国籍,自嘲是唯一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英国作家。因凡特自己也做翻译,曾翻译过《都柏林人》;同时,与两位译者合作共同翻译了《三只忧伤的老虎》英文版。据范晔介绍,因凡特认为相比西班牙文,英文有更多的表达空间,在翻译时重写了很多,因此该书英文版比西班牙文版长。因凡特自己说,《三只忧伤的老虎》是另外一本书,它诞生于被翻译出版的1973年,而不是小说创作的1967年。在范晔看来,很多人把《三只忧伤的老虎》与《尤利西斯》相提并论,是因为作品中都充满对于语言的迷恋,同时都有很强的本地色彩;另外,“如果说《尤利西斯》是漫长的一日,那《三只忧伤的老虎》可能是漫长的一夜。因凡特虽然写了很多夜晚,但其实都在无形当中投射到了一个漫长的告别的夜晚”,范晔觉得,也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哈瓦那夜店版的《追忆似水年华》”。
提到拉美文学,可能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魔幻现实主义,它是辨识拉美文学的标签,但也可能会遮蔽掉很多东西。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表述和分期,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但大家公认的代表人物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此外,靠着一部中篇体量的《佩德罗·巴拉莫》和一部短篇集就奠定了在20世纪下半叶整个西语文坛地位的墨西哥作家鲁尔福,以及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等,也被划分为魔幻现实主义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
在范晔看来,当代拉美文学写作呈现出非常多元的面貌,很难再用一个标签来概括。比如,几乎很少有人会把同为拉美作家的博尔赫斯或科塔萨尔归类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在魔幻现实主义之外,还可以理出另外一个线索,范晔称其为“拉普拉塔河流域小说”或者“拉普拉塔河流域幻想文学”。这条线索的作家集中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从基罗加到近几年重要译介的罗伯特·阿尔特,再到博尔赫斯及其死党比奥·卡萨雷斯以及科塔萨尔,他们的作品可以被称为幻想文学,与魔幻现实主义相比有比较明显的不同。《三只忧伤的老虎》与《百年孤独》同在1967年出版,但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谈到拉美文学时另一个绕不过去的概念是所谓的拉美“文学爆炸”。对于“文学爆炸”的具体断代,学界说法不一,很多人倾向于1960年前后,很多熟悉的作家如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等人的代表性作品基本上都诞生在上世纪60年代。因凡特的代表作也创作于这一时期。据范晔介绍,曾有人问过因凡特怎样看待“文学爆炸”和其中的一些作家,因凡特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学爆炸”,只知道什么不是文学爆炸,“文学爆炸肯定不是一种文学运动”,他说自己不参加什么俱乐部,对这种互相吹捧的文坛“圆桌骑士”也没有兴趣。“‘文学爆炸’里面很多作品他都不太看得上。他觉得真正有价值、能流传后世的就是《佩德罗·巴拉莫》,另外就是博尔赫斯。他说如果过一百年拉美文学还有人看的话,那就是看博尔赫斯的,其他作品他一个也没提。他这个人性格也是这样的,即使佩服他也不太愿意说出来。他跟文学爆炸的关系可以说是若即若离,比较边缘化,他整体的写作也都是比较边缘化的状态。”虽然被视为“文学爆炸”的边缘人,因凡特的作品还是很快就被经典化。1997年,他获得了西语文学最高奖“塞万提斯奖”;在剑桥大学的《拉美文学史》中,也有专门章节介绍因凡特及其作品。“他永远是一个边缘的经典”,范晔说。
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