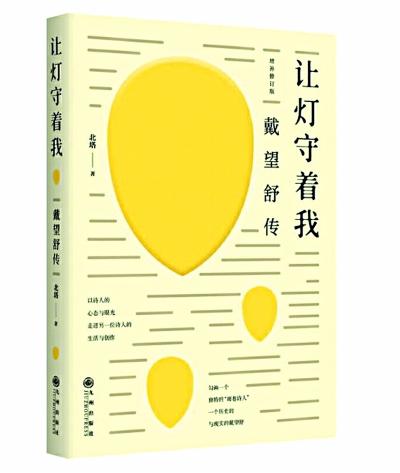
《让灯守着我: 戴望舒传》 北塔 著 九州出版社 | 领读文化
北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也是诗人、诗歌评论家。他的《让灯守着我:戴望舒传》初版于16年前,今年适逢戴望舒逝世70周年,增补修订,重版以作纪念。
这部传记并非通常的线性叙事作品,而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每章都附有大量注解。对于戴望舒作品诞生的时间、背景及其牵涉的人生际遇与人事背景,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之上,详加对比,细节考证,功夫扎实,论断力求客观公允。戴望舒是诗人,北塔也是诗人,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阐释分析深刻独到,亦是本书一大特色。
除了这部传记,北塔还作为编者整理了戴望舒诗选,题名为“鹿守我的梦,鸟祝我的醒”。这个标题来源于戴望舒的诗歌《古意答客问》:“渴饮露,饥餐英;/鹿守我的梦,鸟祝我的醒。/你问我可有人间世的挂虑?/——听那消沉下去的百代之过客的蛩音。”诗歌流露人生的大寂寞与澄明清净的心境。这在戴望舒另一首名诗《灯》里也有所表现:“灯守着我,劬劳地,/凝看我眸子中……这里,一滴一滴地,/寂然坠落,坠落,坠落。”北塔摘取这两句诗分别作为诗选和传记的书名,构成了互文,悄然表达他对戴望舒的理解。
灯,极具象征意义,是戴望舒孤寂独坐的陪伴者,也是诗人倾吐内心的对象。据总角之交兼诗友杜衡回忆,戴望舒开始写新诗大概是在1922年至1924年之间,“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诗当作另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戴望舒在青少年时代就投身于文学团体与文学刊物的创办,因大环境恶劣而屡遭失败。正如杜衡所言,“虽然有时候学着世故而终于不能随俗的望舒”在应付“复杂”“苦恼”“重压”“幻灭”“虚无”之时,有多么难堪和挫败。作为一个木讷内向、生于江南,并沉浸晚唐五代诗风熏养,始终对诗歌有着敏锐感受的文学青年,戴望舒很早就认同法国象征派的审美意识,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诗观。
成名作《雨巷》创作于1928年,在戴望舒23岁的时候,他成为了大众熟悉的“雨巷诗人”。《雨巷》的核心意象,是对南唐李璟“丁香空结雨中愁”的改写,诗句蕴含中国古典美学的情致,它的抒情方式也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传达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彷徨和烦忧的困境。它还有一种抑扬顿挫的音韵之美,叶圣陶称赞该诗“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雨巷》获得欢迎不久,戴望舒却很快地做了“音乐的成分”的反叛者。他在《诗论零札》里说道:“诗不能借重音乐”“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戴望舒尝试用随意自由的现代口语创作了《我的记忆》:“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这首名诗不被韵脚束缚,内在节奏的变动,接近于散文的语感,达成了诗歌对日常生活的敞开。《我的记忆》开了中国1930年代现代派新诗的一代诗风。
戴望舒不断追求他的诗歌理念,到了1940年代,他的诗风又发生了变化。“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写下这些句子的诗人,与那个喜欢描写泪水、哀愁、忧伤的年轻人相距已远。可是,如果没有最初那些尚且稚嫩、略显造作的诗句,又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深沉与成熟。这是戴望舒对“永远不会变质的‘诗之精髓’”的深切把握,也是他面对民族苦难、因抗日举动被捕入狱遭受虐刑之后的了悟。他不断地走向“大我”,走向更广阔、更深邃的诗歌空间。
读《萧红墓碑口占》,很少有人不会为之感动。短短四句:“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仔细体会这些字句,“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头边”而不是墓边,“红山茶”而不是别的什么花,漫漫长夜里生与死的对话,干净、朴素、洗练,不可尽言的克制,对人生苦难的超越与升华。
1942年1月,萧红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病逝,草草地葬在浅水湾。这一年11月及此后,戴望舒屡次拜谒萧红墓,诗歌确切写作于何时,已经很难确定了。戴望舒在1948年把它收入最后一部诗集《灾难的岁月》,并标注为1944年11月20日。北塔指出,实际上,此诗在9月10日的《华侨日报·文艺周刊》第33期上已经发表。当时,第二行是“到你头边偷放一束红山茶”。一个“偷”字的删减,足见局势的险恶,删去“偷”字,也更见诗风的沉稳。围绕这首诗歌诞生的过程,我们看到了戴望舒在港期间的活动,以及他与端木蕻良、叶灵凤等友人的交际。北塔非常重视戴望舒作品的具体创作时间,在细枝末节上详加推敲,纠正了一些不实叙述,因为这些时间关系到创作观念变化的契机,也牵涉当时文坛动向与引领者。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情感经验密不可分。戴望舒中学时与杜衡、张天翼等人同学,大学时与施蛰存、丁玲同学,他与梁宗岱、卞之琳、冯至等人合作创办过新诗刊物,又是左联抗日的积极分子,与艾青等人交好,在港期间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戴望舒的朋友圈无疑是中国现代派诗人的一处“堂口”。戴望舒一生有过三段恋情,他苦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可惜襄王有梦神女无心;31岁时与小说家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38岁时两人离婚不久,他与女职员杨静闪婚,后杨静于1948年与人私奔。北塔说,望舒认为世上最美好的人生是有一个稳定的家,自己能集中精力创作和翻译,写自己想写的,译自己想译的,他一生都在追求这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但却一直无法得到。北塔没有为戴望舒避讳,感情的不顺主要仍是戴望舒的缘故——这个对诗歌极度敏感的人,对待爱人却十分迟钝,在家庭关系处理上难免粗暴并且大男子主义,他的失落、无限的眷念之感,只能借助《我的记忆》这类诗作咀嚼苦涩,找寻栖所。
戴望舒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并不多,只有区区92首,但他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很大的。除了写诗,他还翻译。他把象征主义尤其是波德莱尔的诗歌翻译出来,他向中国读者介绍魏尔伦、耶麦、果尔蒙、瓦雷里、阿波利奈尔等诗人。继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之后,他又致力于翻译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诗歌,尤其他翻译的洛尔迦诗歌一直为人称道。后来,他还转译了叶赛宁等俄罗斯诗歌。翻译与创作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北塔在他主编的那部戴望舒诗选序言里说道:“望舒的诗和译诗是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化或者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和样本。”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林颐